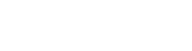《民法典》背景下药物临床试验中的侵权责任(二)
发布日期:2022-08-10 浏览次数:667
二、药物临床试验侵权纠纷适用侵权责任一般条款
基于前述,药物临床试验区别于诊疗行为,具有独立性,显然不能适用《民法典》中医疗损害责任的条文。在比较法上,存在无过错原则适用的情形,欧洲部分国家也有过错推定原则的适用,但这在中国法上都需要以明文法律为基础。如果没有上述两种特殊规定,那么受试者请求损害赔偿就要求诸《民法典》第1165条,即一般条款。然而,《民法典》新增第1008条对人体试验进行了明确规定,该条款在此类纠纷中效力如何?与第1165条在适用上存在怎样的关系呢?
(一)《民法典》第1008条的适用分析
《民法典》第1008条是一种程序性要求的规定,虽然是明确针对临床试验的条款,但该条缺失法律后果。该规定并未说明未经受试人同意或研究者等主体未尽到告知义务的情况下,导致的法律后果如何。
纵观整个人格权编的条文,不少都是概括性使用“民事责任”“过错”“赔偿损失”等术语,绝大多数并未作请求权类型的区分,已经是越俎代庖规定了侵权责任编的内容。第1008条主要是在受试者权利的角度做出正面规定,明确其知情同意权,此处的知情权属于健康权的内容,当该权利受到侵害但未受损害时,已然具备违法性。但实践中,诉至法院的纠纷绝大多数都是受试者已受到损害。这种情况下,有学者认为受试者不仅可以行使(一般)人格权请求权也可以依侵权责任进行救济,此时是请求权的聚合。另有学者认为,人格权请求权只在未构成侵权时发挥效用,与侵权责任的救济毫不相干, 损害赔偿与人格权请求权没有任何牵扯。但无论采取哪种观点,第1008条都不是人格权请求权条款,在人体试验纠纷中很难发挥独立的救济作用。人格权编采取“侵权—保护”的模式,以此实现受害人取得人格权请求权的效果。在司法实践中,侵权请求权展现“大包大揽的状态”,已经弱化了人格权请求权该有的功能。试验受试者的人格权遭遇不同形式的侵害,但受试者的生命、身体、健康等未受损害时,仍可以行使人格权请求权。
在人格权编,因人体试验侵权情形可以追溯到《民法典》第995条的参引规范,“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所指向的参引对象多数情况下还是《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药物临床试验在受试者已经受损害的情况下,最终还是需要求诸侵权责任一般条款。但不可否认,第1008条的适用在侵权责任的构成方面———尤其是过错与违法性(对知情同意的具体分析)的认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辅助作用。
(二)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的终局选择
《民法典》出台前,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状态。有学者在2012年就已经指出,解释论下临床试验侵权纠纷的解决应选择过错原则不容置疑。就当时实施的《侵权责任法》而言,这是适应制定法的最佳选择。但一直以来,仍有不少学者认为过错原则之下对受试者保护力度存在不足,应借鉴比较法经验,规范应当更为精细化,依据《宣言》所划分的治疗性试验与非治疗性试验进行归责原则的选择。比较法经验值得分析,但在后《民法典》时代,从解释论视角下解决临床试验纠纷显得尤为重要。
(三)比较法上的经验探究
对于这类纠纷,比较法上对归责原则的讨论异常激烈。美国司法实践中选择了无过错责任原则,这与其具体国情有关,因其社会保障方面较为完善,以行政方式可以保证良好的补偿方案。该观点认为,过错责任原则的本质前提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与发起人(研究者)和受试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是相矛盾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典型是《人体试验法》(荷兰)做出的规定,但与之匹配的是以完善的配套保险作为强大支撑。还有一种综合二者优势的模式,最具代表性的是法国《生命伦理法》的分类选择解决方案,这一法律同时解决了受试者因果关系证明困难的困境。归责原则的选择建立在衡量两种试验差异的基础上,可以很大程度避免将“临床试验”整体大而化之。如前文所述,《宣言》已经对试验进行分类,第一类中健康受试者的身体对新药疗效没有客观期待或追求,采用“无过错原则”;而第二类中携带与新药相关疾患的受试者,具有一定的不确定疗效利益,选择“过错推定原则”。以下将选取综合性的法国模式,就归责原则选择背后所考虑的因素进行详述。
绝大多数受试者本来就对医学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有很大困难,而试验所使用的药物基本上又代表着所属领域较为前沿的技术,受试者举证难度可见一斑,很难得到有效救济。众所周知,新药研发一旦成功将带来巨大的盈利回报,受试者作为试验的基本载体虽然承受了健康风险,但却不会获得相应的显性回报。一方是资金实力雄厚的药企、医疗机构抑或是社会地位较高的医疗人员,另一方可能是仅仅需要获得免费药物就“被迫”参与试验的弱势受试者……凡此种种,侵权责任构成的认定应当倾向于保护受试者。
非治疗性试验体现的是更纯粹的奉献精神,所试验的药物对受试者无益,他们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前述比较法上的特殊安排,都致力于将保护的力度向受试者倾斜,而做到全面良好的保护、营造安全的试验环境是倡导和鼓励这种行为的事实基础。
在治疗性试验中,受试者罹患相关疾病(即该新药物所指向疾病),一般也在期待药物并不特定的药效,尤其在一些绝症、治疗药物缺乏或价格昂贵等场合下,此处的药效也代表着一种具有不确定性的利益。 同时,我们也应该顾及试验投入现状,试验的资金占整个药物研发资金的最大比例,如最近一则报道显示,药物在试验过程中所耗费的成本逼近研发总资金的七成,试验成本投入极高。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需要药物研发的积极态势,肯定了受试者无私奉献的道德价值,但不能因为发起人和研究机构处于优势地位就完全不顾及这些主体的利益而挫伤其研发积极性。长远来看,这一行业的发展关系到我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福祉。故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平衡试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对比医疗损害中几个过错推定的情况,相较于诊疗资料来说,试验资料的掌握与了解其实更加困难,采取过错推定的模式也无可厚非。
(四)适用《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
上述比较法分类选择归责原则的做法值得借鉴,但可惜的是这在我国并没有充足的现行法律依据,选择无过错责任原则或过错推定原则必须具备制定法依据。另外,《民法典》第1008条虽直接针对临床试验进行规定,但显然没有对以上两个特殊归责原则做出选择,受害人不能请求人民法院适用其中的任何一个。在我国制定法框架之下,最终选择还是侵权责任一般条款中的过错责任原则,即适用《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为了最大程度达到上述比较法对受试者倾向性保护的效果,在遵循《民法典》规定的过错原则前提下,可以在适用法律时,对侵权责任构成各个要件认定进行特殊安排。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药物临床试验的风险不可预见,当事人竭尽所能说明解释和预防,也可能会发生受试者健康受到损害甚至死亡。在适用过错原则的前提下,如果各方主体均无过错,此时就有了公平原则的适用空间,发起人、研究机构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相应的补偿。《药品临床实验管理规范》(GoodClinical Practice,以下简称 GCP)第39条同样规定在研究者和临床试验机构无过失的情况下,发起人作为最终的利益归属方,在投保之余,担负医疗等费用,其性质仍旧是补偿而非赔偿。发起人应当为受试者购买保险,否则应当承担受试者的相应损失。发起人对于除医疗事故之外不可控的人体试验造成的损失,承担法律和经济上的补偿。司法实践中,就有法院依据鉴定意见书,认定发起人、研究者在试验中无过错,但受试者疾病不能排除与药物试验的不良反应有关,依据 GCP 的规定判定被告给予原告经济补偿。这也是《宣言》中“有利原则”的应有之义。
(作者:付琦,张平华,来源:《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免责声明:本网部分文章和信息来源于国际互联网,本网转载出于传递更多信息和学习之目的。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立即联系网站所有人,我们会予以更改或删除相关文章,保证您的权利。
 0
0
该内容非常好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