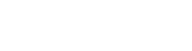《民法典》背景下药物临床试验中的侵权责任(一)
发布日期:2022-08-09 浏览次数:648
摘要 COVID-19疫情进一步推动了药物临床试验的开展,而此类侵权纠纷的裁判在司法实践中呈现出混乱的状态。在《民法典》出台的背景下,应明确临床试验行为并非诊疗行为,不能适用医疗损害责任规则,需要协调人格权编与侵权责任编的适用,做好受试者、发起人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利益衡量,全面保障受试者的权益.《民法典》第1008条直接表明了规范对象,却没有规定法律后果,难以单独发挥损害救济作用。另外,不能直接借鉴比较法上适用特殊归责原则的做法,药物临床试验侵权责任请求权基础仍应是《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适用过错原则。在认定侵权责任时还应考量《赫尔辛基宣言》的价值取向,准确认定其中的过错与违法性,可利用盖然因果关系、善良管理人等特殊标准,以平衡当事人利益。
关键词:药物临床试验;侵权一般条款;《民法典》第1008条;临床试验侵权责任。
医学自起源至今,药物临床试验在其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医学发展早期就有关于药物试验的探索———神农尝百草,但直至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人类仍旧不能对药物临床试验产生的实际效果进行把控,此类试验与受试者的健康乃至生命密切相关。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药物临床试验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开展。据“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网站数据显示,已有938项新冠肺炎相关的临床研究在我国开展,其中涉及大量临床试验。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人格权编第1008条已经做出了专门规定,但受损害的受试者寻求法律救济的最终路径仍在侵权责任编。因审判实践呈现的是诊疗行为与临床试验行为混淆、法律规则适用混乱的状况,所以在《民法典》背景下,药品临床试验侵权责任的构成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民法视域下药物临床试验的特性
药物临床试验(以下简称“试验”) 是以人体为对象,意在发现、验证试验药物的临床医学、药理学以及其他药效学作用、不良反应,或者试验药物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以确定其疗效与安全性的系统性试验。这一概念不包括其他类别的人体试验,《民法典》第1008条规定的三种类型都属于人体试验,但本文的探讨范围仅限定在药物方面。
(一)性质:试验行为独立于诊疗行为
药物临床试验区别于诊疗行为。试验涉及发起人、研究者、受试者等多种主体,诊疗行为则发生在医患间,两组关系常有交错(多数情况下表现为研究者—医生、受试者—患者双重身份交错的状态),这是当前造成二者在法律层面易混淆的一个重要原因。厘清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考察两者区别,可以发现:其一,在行为目的方面,当患者求诸医院,需要的是一种疾病的精准治疗方法或手段,医务工作者的行为目的当然是针对该特定患者、特定疾病做出可靠的诊疗。而试验所针对的对象并不是某一个或一些人,它体现着很强的广泛性;试验中使用的药物主要意图也不在于对患者的诊疗,最终目的还是要归结到验证预期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其二,在风险程度方面,诊疗行为中医生所进行的治疗行为基本都成熟稳定,具有较高安全性;医疗风险整体相对小、可预测性相对强,疗效、结果基本确定。而“试验”二字从文义上理解亦是对完全未知的探索,而这种“未知”叠加作用于复杂的人体,所产生的风险也在放大。
诊疗行为所引发的纠纷,由《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六编)专章规定。而明文规定此类试验纠纷的《民法典》条文在人格权编,应与侵权责任编衔接并综合适用,两者裁判依据完全不同。值得注意的是,从人体试验的宏观角度来看,综合现有证据无法准确区分二者时,应按照人体试验处理。这就为此类纠纷的性质界定指明了方向———侧重将受害人推定为受试者以获得更高标准的保护,法院若无充分依据不能径行认定为医疗损害纠纷。
(二)类型:治疗性试验与非治疗性试验
在临床试验领域,《赫尔辛基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做出了“二分模式”的分类,根据目的效果,将一部分试验归为非治疗性试验(I 期),另一部分归为治疗性试验(Ⅱ期、Ⅲ期)。这种区分是在医学视角下进行的,但不同试验在受试人的选择、药物试验安全性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潜在影响了欧洲不少国家在民事侵权救济中归责原则的选择,也是我国法律适用应当考虑的因素。
非治疗性试验的内容与受试者本身的既往病史或当前身体状况并无直接关联,研究者参与其中并无疾病疗效的追求。这一试验是初步性的,I期药物临床试验属于非治疗性试验,需要的试药人员并无罹患该试验药物所指向的疾病,是身体健康的受试者。 此阶段,受试者所体现的作用是提供了解药物在人体反应机制的载体,以便进一步探索人体对药物的耐受力和代谢规律等,而无意于研究药物的治疗效果。此阶段是药物第一次作用于人体,危险性较高。治疗性试验也被称为具备诊疗目的的试验行为。与常规诊疗行为有类似之处,存在探索疗效之目的,但其特殊性在于使用的新药物或方法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此种试验针对的是罹患该种药物相关疾病的患者。Ⅱ、Ⅲ期临床试验隶属治疗性试验,而不同于非治疗性试验;此时已经进入确定试验药物的安全性和治疗效果的阶段,这类试验的核心特征与内在要求是针对相关疾病(新药所指向的疾病)的患者开展。这个阶段最易造成司法实务中试验行为与诊疗行为认定混淆的问题。
(三)侵权行为人:发起人、研究者、研究机构
试验所涉及的并非简单的双方主体,需要结合具体案件事实进行判断,但在绝大多数纠纷中涉及的主体较为固定。
发起人是指在一定研究基础上着手进行药物临床试验,负责试验发起时接收审查的相关事项、实验过程中事务管理、以及财务流水记录与核验的组织,也称申办者。他们在试验期间承担重要责任,应积极投保,全程必须尽可能保证受试者身心免遭伤害。临床试验机构(如医院)受发起人委托,基于临床试验协议形成委托关系,委托信息披露于受试者,发起人亦参与到二者法律关系中,自然不能以其仅是委托人而免责,本文暂不在合同范畴内过多着墨。该机构执业的研究者进行试验的具体操作,属于职务行为;临床试验机构要对试验的进行和受试者的安全承担责任,承担用人者责任;研究者作为发起人和受试者中间的重要一环,应具备较高的医学专业技术水准。另外,研究者的日常工作包括完成每天的试验记录与报告、数据分析等。侵权责任构成的分析主要围绕发起人、研究者、研究机构展开。
合同研究组织、伦理审查委员会等机构的存在对试验本身而言具有必要性,但因其附属性或中立性等现实状态,在侵权责任纠纷中并不是独立、适格的民事责任主体。
(作者:付琦,张平华,来源:《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免责声明:本网部分文章和信息来源于国际互联网,本网转载出于传递更多信息和学习之目的。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立即联系网站所有人,我们会予以更改或删除相关文章,保证您的权利。
 0
0
该内容非常好 赞一个
- 上一篇:《民法典》背景下药物临床试验中的侵权责任(二)
- 下一篇:律医一周动态第39期